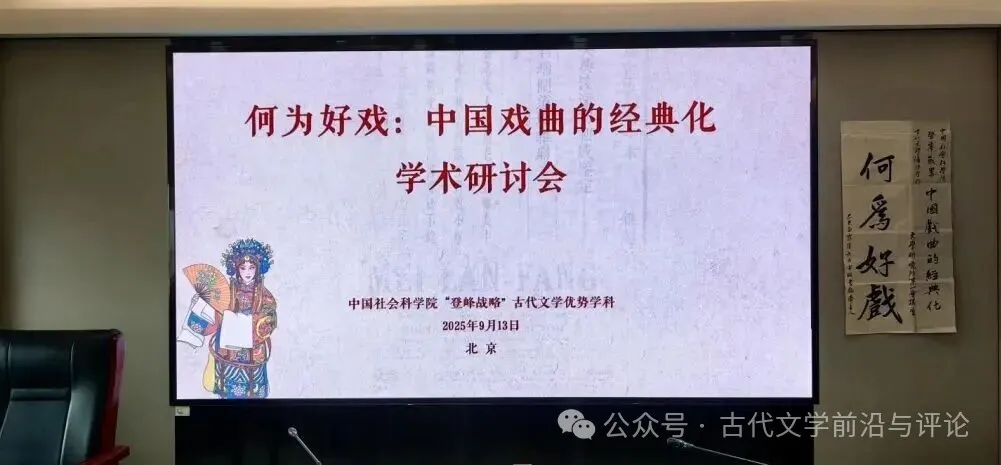
从王实甫《西厢记》、高明《琵琶记》、汤显祖“临川四梦”,到清代双峰并峙的《桃花扇》《长生殿》,再到近代梅派京剧《贵妃醉酒》等,中国戏曲经典之作代不乏见。经典剧作的命运颇为相似,大多问世不久即受到文人的热议、追捧,或被改编、排演于氍毹之上赢得满堂喝彩,这些剧目究竟缘何吸引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就引出了“何为好戏”“哪些作品是经典剧作”“戏曲如何成为经典”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好戏”与“经典剧作”的含义和外延不尽相同,当这一对“一体两面”的概念相遇之时,就促使我们从文学文本和舞台艺术两个维度去审视“经典在案头,好戏在场上”的内在意涵,并由此进入对“中国戏曲的经典化”学术话题的讨论。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凸显交叉学科研究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于2025年9月13日在北京举办“何为好戏:中国戏曲的经典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中青年学者展开了深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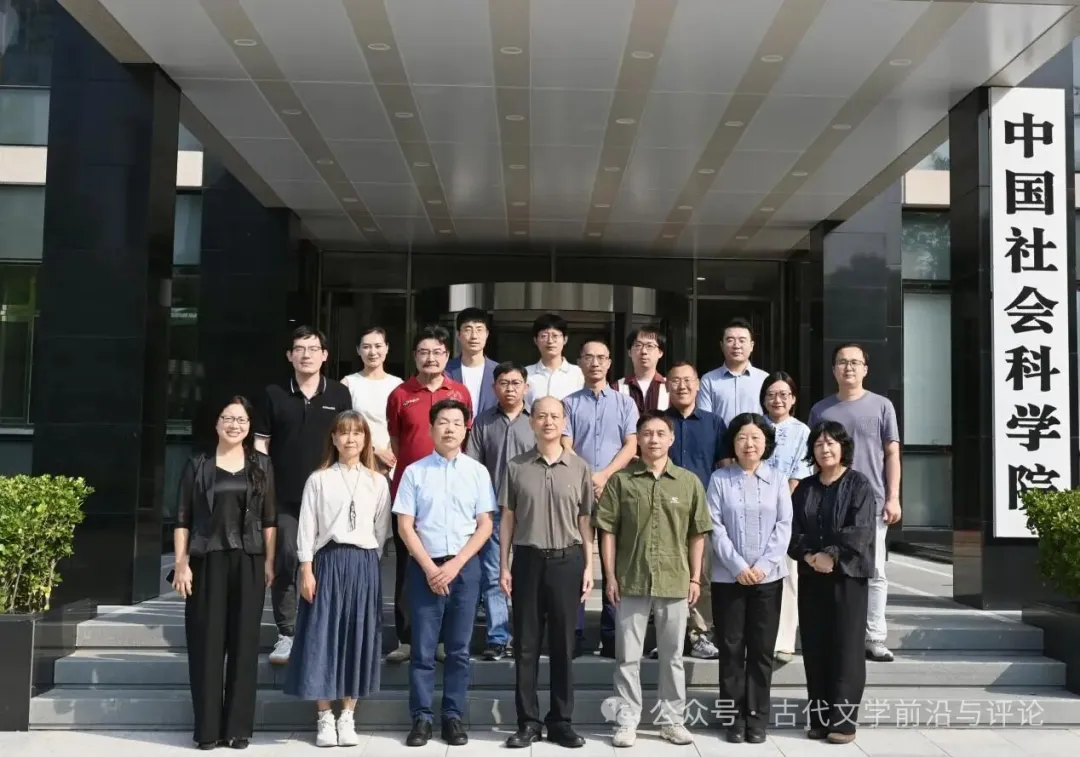
开幕式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饶望京致辞,他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和全体同仁,对应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他表示文学研究所一向重视中国戏曲研究,古代文学优势学科围绕“中国文学经典与中国古典学”这一创新方向,积极推动中国戏曲经典化的思考,今天举办的“何为好戏:中国戏曲的经典化”学术研讨会,旨在促成不同研究方向的戏曲研究者的思想碰撞与学术交流,拓展对“戏曲经典化”的思考。饶望京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在戏曲研究方面传统深厚,几代学者不断耕耘,陆续编成《古本戏曲丛刊》十集,向学界推出诸多重要论著,推动了中国戏曲研究的进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提高中国戏曲经典作品的整理、阐释、研究、传播的力度和水平,从而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在当前进一步推进中国戏曲经典化研究有重要时代意义。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主持。

研讨会第一场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李超编审主持。
中国戏曲学院吴新苗教授作题为《何为好戏:戏曲经典化的要素》的发言,发言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武迪代为宣读。吴新苗认为在关于“经典”的研究和论述中,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经典”是由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所决定的;一种认为“经典”并非取决于作品本身,而是由意识形态、权力结构等建构起来的。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什么样的戏才是好戏,才能成为经典之作,有两个要素值得注意。一是话题性,所表达的内容是对在人群中广泛传播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话题、社会话题、民族情感心理话题的呼应,话题是一个召唤的结构,引起人们的注意、思索、共鸣和谈论;一是细节化,具有话题性的叙事往往存在众多文本/版本,某一个文本/版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经典,关键之处还在于细节的处理。
中山大学陈志勇教授作题为《“琵琶记现象”:戏曲经典的接受分化与其生成机理》的发言,他指出一部经典戏曲作品诞生后,它就以开放的姿态进入读者阅读接受的环节,读者通过文本符码的解读,去感受、探索文本并阐明其意义,会导致阅读过程出现文本的“多义性”。读者所体悟或揭示的多种意义,既有可能重现或涵盖作者的意图,也可能是对作者意图的偏离或扩大,《琵琶记》的接受史亦是如此。一部分读者能体会到作者高明通过《琵琶记》为蔡伯喈翻案的良苦用心,但更多读者却根据各自的立场和感受对这部名著做了新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接受向度:既有对原著“全忠全孝蔡伯喈”的顺向接受(如全孝说),也有对原意的反向接受(如讥刺说、嘲骂说)。同时,在文本立场上,文人雅士坚持对元本《琵琶记》的进行复原;普通读者以“时趋”为导向,对文本进行“通俗化”改造。明清时期读者接受路向的分化,与高明为蔡伯喈翻案的意图和“源文本”形貌构成强烈的张力,成为《琵琶记》阅读史上一个极富兴味的文化景观,或可称之为“琵琶记现象”。这一现象对于考察戏曲经典作品的雅俗分化与读者接受具有典型意义,它不仅勾连起文本生产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而且能更好理解文本流动、改编、阅读和批评的多重面相。
河北大学都刘平以元杂剧的经典化为讨论中心,发表题为《元杂剧经典化在元代的进行》的发言。他以西方学界对元杂剧的质疑为切入点展开讨论,指出学界在元杂剧研究中更多依据明人刊抄的元杂剧文本,不少学者认为“元杂剧”是明代人的“发明”和“建构”,由此论定元杂剧经典地位的确立是明人“宗元”复古思潮的产物。这不仅否认了元杂剧的真实“存在”,也将元杂剧成为“一代之文学”经典的功劳全归于明人。考辨元代文献可知,元人一开始就已自觉充分地认识到元杂剧的特有价值,这种认知并非仅存在于杂剧作家圈,至元代中后期已成为不同阶层文人群体的共识。元杂剧经典地位的确立并非“萌芽”于明代,明人之于元杂剧经典地位确立的功劳不是“建构”,而是元人群体认知的必然结果,其贡献也仅是顺势而为和“推波助澜”。
北京大学陈均教授的发言《情感与艺术:〈牡丹亭〉的三重制作》,从文学文本和舞台艺术角度讨论了中国戏曲经典《牡丹亭》的“制作”。他认为《牡丹亭》成为经典的过程,经过了作者、阅读者、表演者的三重“制作”,作者汤显祖创造性地将《杜丽娘记》这一类的话本改编为兼具“奇”“情”的传奇作品,趣向与姿态各异的阅读者进一步阐释与拓展了《牡丹亭》的意义,表演者则发掘与增添文本的表现力,并与不同的时代状况相适应,从而“制作”出不同面向的《牡丹亭》演出版本,共同构成了作为经典的《牡丹亭》。在这一生产机制里,“情感”与“艺术”的因素相互交织,并成为其核心要素。
中国人民大学张一帆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国剧经典剧目研究”教学体会》为题的发言,介绍了“国剧经典剧目研究”课程的总体情况。本门课程总目标为:选取一定数量的京剧、昆剧经典剧目(“国剧”),包括传统剧目、古装新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通过对个案的解析,总结各剧目在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各个创作环节的基本规律。课程具体关注的方面包括:一、戏剧创作背景:剧目产生的历史沿革;二、戏剧的思想性:三观中主要关注价值观,并主要把握历史的维度;三、戏剧的艺术性;四、戏剧的影响、传播范围与深度。
研讨会第一场发言的讨论环节,参与本场发言的陈均、陈志勇、张一帆、都刘平及与会其他嘉宾围绕“经典”“好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如何判断认识一部剧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典地位的起伏变化等话题展开讨论。


第二场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吴刚研究员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王小岩作题为《金圣叹〈西厢记〉评点的阅读伦理》的发言,他尝试借鉴 J.希利斯·米勒的“阅读伦理”,探索金圣叹在晚明《西厢记》阅读的“众声喧哗”中构建阅读共识的努力,挖掘金圣叹阅读伦理的特点。他认为,J.希利斯·米勒选择德里达的述行性理论,指出“阅读的伦理就是文本中的文字对大脑以及读者的话语所产生的能量”,“是道德上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要求人们不管说什么,都要以某种方式遵从我们所谈到的语言命令所表达的真理”。阅读行为势必改变读者的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每次阅读或教学一部文学作品时,都可能打破大学社区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由此,J.希利斯·米勒提出“公正地阅读”,“公平对待文本,当我阅读时能够达到小说对我提出的要求”,“公正地阅读并不仅仅是确实了解小说,也是正确理解小说,它还要以阅读为基础,以负责的方式做出回应,并确实有所行动”。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开篇针对“淫书”论发难,已经切入阅读的伦理问题,而他的评点也可视为“公正地阅读”行动。借由阅读的伦理视角,不仅能揭示金批《西厢记》的时代性,也有助于理解《西厢记》经典化进程的曲折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芳研究员同样选取《西厢记》这一经典剧作为研究对象,作题为《阅读〈西厢记〉:弘治刊本〈西厢记〉“附录”探论》的发言,尝试从阅读角度来讨论《西厢记》的经典化问题。她指出,现存最早的《西厢记》全本、明弘治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的出版牌记引出一个问题:戏曲剧本的创作为了舞台演出,观看和阅读的体验具有明显的差异。“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是针对配合演出的需求,阅读的需要在于“切须字句真正,唱与图应”,那么,牌记提出的“市井刊行,错综无伦”问题,是一种营销策略,还是实际存在的情况呢?它所确定的文本形制,又是如何实现以阅读目的为指向的呢?对此,李芳指出弘治刊本《西厢记》中,除了曲本本体,还有大量的“附录”,也就是相对于曲文来说的“衍生文本”。如果将《西厢记》视为一本被阅读的书籍,这些“附录”中的内容就与曲文成为一个整体,不可被分割与忽视。对其加以多维度的讨论,有助于理解明代戏曲曲本“阅读”方式与习惯的形成,以及戏曲创作从“舞台”中心转向“案头”中心的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任刚以清初苏州派戏曲为论题,作题为《清初苏州戏曲的典范性意义探赜》的发言。他认为立足于戏曲的综合性艺术形态加以审视,清初苏州戏曲在古典戏曲演进史上有着典范性意义。该一时期的戏曲作家、作品数量庞大,既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等职业编剧,还有吴伟业、尤侗、叶奕苞等业余曲家。他们的身份、经历、趣尚相别,戏曲创作呈现出商业化、文人化分异、共生的局面。因处于戏曲观念由“曲本位”向“剧本位”转变完成之际,其剧作分别在民间戏曲、文人戏曲两个传统中,达成了文学性与舞台性的相对统一,比较接近古典戏曲的本质内涵,是古典戏曲在元代戏曲之外的又一典范形态。
首都师范大学谭笑作题为《〈南曲全谱〉的批评与南戏的经典化》的发言,他认为明万历年间,曲学家沈璟编纂的《南曲全谱》开创性地为例曲增加了大量评注,由此建立起一个以南戏为参照的批评体系:对内使南戏之间互为批评的参照,对外使南戏作为明代文人戏曲、散曲批评的参照。《南曲全谱》蕴含突出的南戏经典化意识,值得深入考察。沈璟借此回应了同时代人共同关注的“名剧之争”话题,为探讨这一戏曲史公案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他超越名剧的范围,从整体上思考南戏的经典化。《南曲全谱》推动了曲谱作为新的曲学批评形态的确立,对于思考曲谱与戏曲史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武迪从生活史角度切入古代戏曲研究,作题为《纪实性戏曲:艺术形式的生活史》的发言,他认为纪实性戏曲是以剧作家本人或朋侪的生活经历为本事创作的剧作,记述着发生在私人生活场域或公共生活场域中的人和事,是融合虚实的艺术形式的生活史。在研究纪实性戏曲时,研究者常因戏曲本事的相近、剧作家及其朋侪生活史料的多寡、解读的差异等主客观原因,而误读纪实性戏曲,以致戏曲本事被“张冠李戴”。同时,作为“景象”存在的生活史真相,被剧作家获知并经由大脑记忆的剪裁加工成为“印象”的生活史,再由剧作家的想象、虚构来填补叙事空白、勾连叙事脉络,最终才能成为纪实性戏曲。因此,在纪实性戏曲的记述中必然存在无法被证实的生活史。而剧作家创作纪实性戏曲,本意并非对生活史的如实记录,而是希冀通过戏曲实现对自我/朋侪的形象及其生活史的艺术建构。
第二场发言的讨论环节,参与本场发言的王小岩、李芳、任刚、谭笑、武迪和与会其他嘉宾围绕着经典作家群体研究、经典作品研究、戏曲曲谱与戏曲经典化和非经典作品的研究思路展开讨论。


研讨会第三场发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高明祥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陶庆梅研究员发表《作为表演艺术的戏曲经典化》的发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表演艺术的戏曲整体衰微。但在21世纪初,以青春版《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复兴,却意外地让昆曲这一更为古老的戏曲艺术,在现代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青春版《牡丹亭》并没有纠结在是“复古”还是“创新”的两难之间,而是以复古为创新、以创新来推动古老戏曲的新生。近年来昆曲演出的复兴,将这一古来艺术的服装、曲调、唱词之美,重新带入现代生活,进而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在明清时代,昆曲主要是在灰砖青瓦的戏台演出,其演出生态高度融入文人的日常生活,面对的观众,也多是欣赏水平极高的文人观众。因而,在当下昆曲复兴的潮流中,综合来看,当下的昆曲演出,面对两组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是昆曲演出与现代观众的关系;一是昆曲演出与现代剧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两组关系,是昆曲在当下时代如何在传承中发展并创造新经典必然面对的问题。
中国戏曲学院林丹从舞台艺术角度讨论戏曲舞台表演的身段和经典化表演形态,她在《戏曲“子午相”的身体美学建构与戏曲经典化的表演形态》的发言中提出,“子午相”作为戏曲表演的核心程式,它具有微观表演研究与宏观经典化研究的双重价值。以“子午相”的身体美学建构为逻辑起点,剖析其从形态到哲理的生成路径,进而论证这种外化的表演形态对戏曲经典化的支撑作用,最终揭示微观表演程式与宏观经典建构的内在关联。“子午相”身体美学建构的核心特征:以身体为载体,融合形态审美、哲学内涵与意象表达。“子午相”的身体美学所外化的表演形态,通过“经典传承—文化标识—时代激活”的三重作用,支撑了戏曲的经典化进程。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王岩作题为《〈碧天霄霞〉考略——兼论迎銮戏与宫廷戏曲的区分》的发言,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碧天霄霞》因其特殊的身世,引起了吴晓玲、叶晓青、陈靝沅等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中,陈靝沅通过不同版本的比对,发现该剧存在异名同剧的现象。在细致的文本比对之后能够发现,《碧天霄霞》错讹之处过多,实在称不上善本。目前所见最为完整规范、抄写细致的本子仍然是齐如山旧藏这套进呈本。但与齐如山当时的判断不同,该本并非“安殿本”,从形制和抄写特征上来看,应该称作“进呈本”更为合适。即该剧是为乾隆帝第三次西巡五台山而作,是当地官员组织民间文人创作的迎銮戏而非宫廷词臣创作的宫廷仪典戏。这也就解释了陈靝沅提出的宫廷演剧中为何存在两个剧情完全不同的《四海升平》的现象。迎銮戏与宫廷仪典戏虽然存在创作主题的相似性,但是它们的创作主体、创作初衷、具体用途、演出场域、内容取材都完全不同。目前为止,还未见迎銮戏作品被用于宫廷仪典戏演出的先例。
中国人民大学王燕教授作题为《京剧英译之嚆矢——司登得与京剧〈黄鹤楼〉英译研究》的发言,发言由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卜嘉辉代为宣读:《黄鹤楼》是中国戏曲传统剧目,该作题材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元代话本与杂剧,其后屡经改编,至今搬演。早在 1876 年京剧方兴未艾之时,《黄鹤楼》就被英国汉学家司登得(G.C.Stent)翻译成英文,成为第一部走向英语世界的京剧剧本。本文在全面考察司登得生平经历和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这部译作的翻译底本、译文特色、选译缘由和文化影响,对于研究京剧的早期海外传播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卜嘉辉的发言《1845年〈灰阑记〉英文全译本研究》也是从戏曲外译角度去探讨戏曲的经典化。他在发言中提出,1845年元杂剧名篇《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完整地出现在了英语世界之中,这就是连载于《皮丁船长的中国杂谈与茶话》(Captain Pidding’s Chinese Olio, and Tea Talk)中的《灰阑,一部中国戏剧》(The Circle of Chalk, a Chinese Drama)。该译本的出现远早于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灰阑记》最早英译本,即1929年由英国作家、文艺评论家拉弗(James Laver)转译的《灰阑:一部改编自中国的五幕剧》(The Circle of Chalk: A Play in Five Acts Adapted from the Chinese)。然而,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1845年版英译本缺乏足够研究,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契机。本文在广泛搜集第一手英文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皮丁船长的生平与创刊背景,探讨此译本的译介特点,分析其中人物形象的重塑,同时联系当时的欧美戏剧生态与中西文化交流,总结该译本的文化接受与学术价值。
第三场发言的讨论环节,参与本场发言的陶庆梅、林丹、王岩、卜嘉辉和与会其他嘉宾围绕舞台表演艺术与戏曲经典化、戏曲外译传播与戏曲经典化等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小组发言之后的圆桌讨论及会议总结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石雷编审主持并作总结。她认为这次会议围绕“好戏”和“经典”展开,设置的主题与分组讨论体现了主办方的学术理路,而这种理路正是戏曲经典化阐释的路径。参会论文不管是宏观的阐释还是依具体而微的作品展开的论述,不管是案头还是场上的角度,都体现出研究者对戏曲经典化历时性的梳理与总体把握,以及对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与学科的前进方向密切相关,具有相当前瞻性,探索性。

最后,全体与会学者就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各自的论题和学术交流的心得体会,分别作简要的总结发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其他京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三十余位青年学者、研究生旁听了本次学术研讨会并作交流。
来源:《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公众号

